|
直面西坡村
在长梁乡西坡村,我找到了杨宝瑞烈士的后代杨忠。75岁的杨忠,身板硬朗,口齿清晰。听说我要采访,他把锄头放到自留地里,对我一摆手,迈开健步把我领到他的家里。这是一处典型的农家院落,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各种农具摆放得有条不紊,三间大正房砖瓦到顶,窗户铮明瓦亮。中堂是厨房,锅灶一尘不染,炊具井井有条。东屋是卧室,三节大柜红漆烁烁,一盘土炕暖气融融。本以为,这样干净利索的住处,定是老伴儿女们帮着归置出来的,不曾想,杨忠妻子早亡,儿女都在县城安家,他已独身多年。两支烟,一盏茶,采访就开始了。提及往事,老人记忆的闸门打开,一股脑道出了那段尘封的历史。解放前的西坡村,是远近闻名的重镇,当时不仅有四面城墙,也有门楼岗哨。杨忠的父亲杨宝瑞,是西坡村的武委会主任,掌管西坡村的大权,明里给国民党干事,暗地加入了共产党。战乱时期,各种势力角逐于西坡一带。国军来了,杨宝瑞假意逢迎,但军粮草料分毫没有,派出的劳力也是磨工耍懒。共军来了,正好相反,杨宝瑞挺直腰杆,分派村民,送粮送草,捎带着鸡蛋布鞋。为不暴露身份,杨宝瑞给共产党办事,都是秘密进行,包括传递军情,用的是鸡毛信。 就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杨宝瑞被村里的叛徒出卖。叛徒里应外合,骗开城门,引着一队国军进了村子。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近三更,玄月躲进云层,群星藏在雾后。几声狗叫,惊醒了杨宝瑞的妻子。妻子捂住激跳的心窝,劝丈夫逃离,丈夫摸了摸身边的娇妻爱子,执意不走。院子里有杂乱的脚步,悉悉索索,如同群狼围猎。七岁的杨忠,被母亲搂紧在怀里,恐惧弥漫在整个房间。砰得一声枪响,窗户中间仅有的一块用来瞭望的玻璃被打了个圆眼,其他窗格里的麻纸嗡嗡乱颤,屋里墙角立着的大缸爆裂,酸菜汤流了一地。紧接着,屋门当啷一声被踹开,一群凶神恶煞闯进屋来。 杨宝瑞被五花大绑,押出西城门。妻子拉着杨忠,哭喊着追赶,眼睁睁看着亲人消失在夜色中。杨宝瑞被押到平定脑包,关进监狱。国民党善用酷刑,几天下来,杨宝瑞皮开肉绽、满身疮痍。杨宝瑞牙关紧闭,没吐露一点信息。伪县长郭玉柱,最终放弃审讯,要求家人三天之内拿烟土来赎人。杨宝瑞虽然为官多年,从未盘剥百姓,就是有点积蓄,也暗中交了党费,哪有什么烟土?家人根本无力赎人。 解放平定堡的战役打响后,正义的炮火席卷而来,城墙上的沙袋被炸飞,城门上的木屑被削掉。城里的国军乱了阵脚,狼狈逃窜。郭玉柱想到了监狱中的犯人,若不处置,城池一破,必然放虎归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斩草除根。郭玉柱下了命令,杨宝瑞被押到二十五号附近一个井坑,一颗罪恶的子弹,后背打进前胸穿出,杨宝瑞英勇就义。一个坚定的无产主义战士,就这样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宝贵生命。数日后,杨宝瑞的大舅子,赶着马车,把他的遗体装进一个柜子,拉回西坡,葬在村西的山上。 烈士倒下了,刽子手也难逃清算,平定堡将要被攻破时,郭玉柱用炒熟的豌豆烫伤自己的脸,试图用毁容的手段逃避惩罚。他趁着夜色,逃出城去,骑马一路狂奔。没走多远,就被解放军战士发现擒获。恶贯满盈的伪县长,被押到东坡村正法,剃了光头后,绑在柱子上,批斗会还没开完,愤怒的群众涌上去,已将其揍了个半死。最终,在一条臭水沟里,郭玉柱被执行死刑。 西坡解放后,另一个被执行死刑的人叫孙继民。这个叛徒,出卖了为共产党办事的村长李全。李全得知国民党要抓他后,东躲西藏,但最终听信了同村人孙继民的话,被骗到野外杀害。孙继民制造了震惊全县的东坡惨案后,即到国民党处邀功。东坡解放,孙继民被我党控制,五大三粗的孙治安员,举起大刀,一刀结果了这个叛徒的小命。 解放后,政府追认杨宝瑞为烈士,并发给杨家一斤白糖和一个奖状。杨家依然贫困,杨忠尚且年幼,还有个年迈的爷爷。杨忠的母亲,上有老下有小,一个女人无力支撑家业,为了全家不至于饿死,无奈改嫁。杨忠16岁时,已经有独立劳动能力,就离开母亲和继父,自己撑起家业,并赡养爷爷。几年后,杨忠靠着勤劳和坚韧,打拼出自己的天地,娶妻生子,逐渐过上了好日子。一晃许多年过去,妻子过世,儿女成家,杨忠独自守在家中。儿女们劝父亲搬到县城居住,但杨忠不愿离开西坡,毕竟,这里是他的根之所在。这片故土,洒过他太多的血泪,埋过他太多的悲情。杨忠是个要强的人,他是烈士的骨血,他想向他的先人那样,挺着腰板面对世间的苦难。他不要子女一分钱,他自己种田养活自己,种山药,点大豆,卖了莜麦也能赚两千块。往年,他还养一头肥猪,但今年没养,今年饲料贵,莜麦2块钱一斤了。 熄灭最后一支烟,喝尽最后一杯茶,我的采访结束了。由于杨忠老人的健硕,这是最顺利的一次采访,也是最清晰最生动的一趟历史课。起身之后,我提出了一个过分要求,想到烈士的坟墓上看看。杨忠老人立马同意,他锁好家门,带着我向村西走去。此时的我,对这座看似普通的小村有了新的认识,我每走一步,都在寻找那个血雨腥风年代里留下的遗迹。然而,那高大的城墙早已坍塌,那窗户上糊着麻纸的老屋早已拆掉。 在村中的小路旁,我看到一眼深井,井沿边,一架老旧的辘轳引发我的兴趣。我向杨忠询问这口井的年龄,他告诉我,这口井从他记事起就有。我努力看了看那口井,想在井边凭空想象出一个形象来,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挎着一把盒子枪,他的目光炯炯有神,双手有力地摇着辘轳,一桶清水从井底缓缓上升。走过他身边的人们,都在微笑着向他打招呼,他们都叫他杨主任。其中一个人,还趁人不注意,把一根神秘的鸡毛塞给他。于是,他挑起一担水,快步走回家。他家的窗户,糊着麻纸,只有中间的一小块玻璃,透进一线明亮的阳光,阳光照在一封密信上。 在村子西头,我看到一块石头。石头是规则的长方形,立在地面,一半长进土里,一半露在外面。石头上,有一个圆孔,圆孔很光滑,被磨损成青色。我猜出,那该是一个拴马桩。这个猜测,得到杨忠的确认。他告诉我,这个拴马桩,是个老物件。我的眼前,顿时出现一匹枣红色的高头大马,那匹马,就拴在那个桩子上。那个高大的男人,解了绳子,上马,出了城门,沿着村西的土路,绝尘而去。他去了哪里?那个地方一定是深山老林,隐藏着一支部队,部队里的战士们,带着黄绿色的军帽,帽子上,镶嵌着一颗红色的五星。 岁月,已经荡平了大部分印痕,西坡村里,唯有这口水井和这个拴马桩,成了历史的见证。它们依然保持着旧有的模样,似乎是专等我的到来,让我管窥一个波澜起伏的时代。这普通的物件,每天在村人的脚步声里,在牲畜的鸣叫声里,默默守望日升日落。或许,司空见惯的西坡人,已经不再注意这两样东西,更不会追究它们存在的意义。但对于历史而言,却是最直观的见证。 出西坡村,沿着一条砂石路西行数里,上了一座平缓的山坡。正值六月,野花野草分外亮丽,绿色的主基调里,杂揉着星星点点的姹紫嫣红。微风拂面,野外的清香举手可捧。抬眼远眺山顶,两架高大的风车,如同两个哨兵,分成左右,护卫着一方水土。顺着杨忠的指点看过去,两架风车的正中间,隐约可见几处土丘隆起,像是土地疼出的泡。 来到近前,是三座土坟,延山脉走向依次竖着排开。杨忠告诉我,上方的是他爷爷,下方的是他妻子,中间的,是他父母。我在中间的的坟前蹲下来,仔细研判石碑上的铭文。碑文很简单,左刻“母孙氏,生一九一三年,故一九五四年五月”;右雕“父杨宝瑞,生一九一八年八月,故一九四八年八月”。这是多么普通的碑文,除了名字和生卒年月,再也找不到其他东西。甚至,连个“烈士”字样都没有。烈士的子孙们,用低调的方式,埋葬了他们的先祖,他们不想把荣光写在脸上,只想把追思深埋心底。 我没来得及带一炷冥香,几张烧纸,也没带花环。我就地捧起一把土,撒在烈士坟头。来年,坟上会开一束鲜艳的山丹,那是烈士重生的鲜血,怒放出来,灿若霞光。 |
|
(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扫码关注沽源网

精彩内容看个够
张家口今日热点

各区县的新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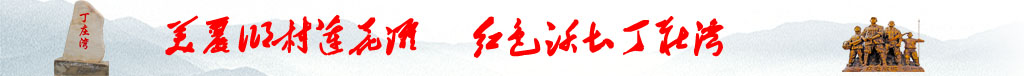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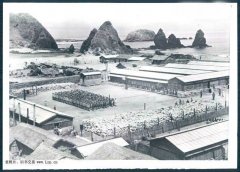
 冀公网安备 13072402000037号
冀公网安备 130724020000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