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路的翠绿葱茏对于沽源人来说已经习惯了,但是微雨过后的那份清新,那份纯粹,还是让人陶醉的。夏天的沽源满眼都是风景,一下东坝,放眼山峦叠翠,远山近景层次分明,薄雾微笼郁郁葱葱。谈笑间便到了马莲口,马莲口及周边长城是明代边塞防御体系的最外的边城,这道边城起到提前御敌的作用。边城蜿蜒在赤城、沽源、崇礼的山间,边墙轮廓在山峦间依稀可见。马莲口东边小山上的墩台依旧挺立,但包砖全无,只是剩下夯土。大家想下去拍照,便停车小憩。登上小山远望,两边山川夹一河谷确是防御之门户,不见当年边塞烽烟,如今确实青盈的玉米,翠绿的麦田。绕墩台细观,去冥想它身上隐藏着数百年的历史,那裸露着的一道道夯土印迹宛如千年古树的年轮,不知记录了多少沧桑,只是已无从破解了。 过了马莲口,便是君子堡,再往前就是马营了。马营,也称马营堡,旧名“震州”,又名“西猫儿峪”。是赤城、龙关管辖的三十二个城堡中最大的一个。《赤城县志》载:马营堡筑于宣德年间,周六里五十步,高三丈五尺,堡楼四,角楼四,铺二十四,堡门四,东曰:“宣文”,西曰:“昭武”,南曰:“广义”,北曰:“恒仁”。比当时的九边重镇开平卫城(独石口城)周还要长三十七步。城堡大,一是它的位置重要,是兵家要地;二是兵马较多,需要较大的地盘吧。实际上马营驻军确实较多,明《北中三路志》记载:当时“马营堡官军一千三百八十二名。”是三十二堡中驻军最多的。而且“马营堡管边墩三十五座,守了官军二百四十五名。腹里接火墩五十六座,守了官军一百八十五名。”这些土墩现在还能看到,每隔几里就一个。马营堡城西面跨在山上。这种筑城方式,也使堡城有一种地势感。不但可以增大了望的视距和视界,同时居高临下有利于扼守山川谷地。马营堡的城垣原来都是包砖的,现在已是被剥的体无完肤了,只是轮廓依旧。马营曾是赤(城)源(沽)联合县第六区公所驻地。这也是我们走访马营的理由。 在马营沿周围城垣转了一圈,夯土依旧,轮廓依旧,只是破败了。村落院墙多为青砖,这都是扒下城墙砌的院墙。走到马营街头,见很多老人堆坐聊天,我们便把车停在旁边,下车走访调查革命情况。和老人们说明来意后,大家都指其中一个人,说他知道,他当年就参加过革命。老人也不客气,便和我们聊了起来。老人叫庞占玉,八十多岁,平北抗日的时候参加游击队,也曾随部队上过坝。当问及解放平定堡的事宜的时候,老人说,他们到达的时候,平定堡已经解放了。由于老人年岁较大,对当年的一些事情记忆恍惚,基本说不太清楚。只是说现在马营参加当年革命的人就剩下两个了,一个是他,还有一个还健在,那人叫王登云。正说着,王登云老人也过来了,王登云老人多年患病,眼花耳背,基本上听不见。和老人闲聊,他们虽说不清当时情况,但总提及一个人,那就是孟政委和宪民村,孟政委牺牲后,把他牺牲的地方改为宪民村。 老人们口中的孟政委,即孟宪铭,这个人我也曾在收集资料的时候看到过,但具体事迹不是很清楚,后查资料得知:孟宪铭河北安茨史家村人。生于1909年。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安茨、永清、宛平、昌延等县参加开辟新区工作。曾担任冀东永清县七区区委书记,1940年到冀热察区党校学习。1941年秋,他以冀热察区党委宣传部巡视员的身份到平北视察时,毅然留在平北工作,任龙(关)崇(礼)赤(城)联合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九、十联合区区委书记,后任县委组织部长。在他的带领下,九、十联合区开辟工作进展顺利,很快打开了局面,建立了区、村政权和地方武装。九、十区分设后,他兼任十区区委书记。为了开辟新区的工作,孟宪铭同志经常单枪匹马,一个人在敌人据点间活动。1943年3月,孟宪铭得了伤寒病。在从孟家窑村转移时,被蚂蚁洼地主白老六告密,驻羊坊日伪特务队长马四秃子带领20多个便衣特务,赶到大沙沟的自然村小沙沟,在石成玉家将孟宪铭抓获。敌人将他押到羊坊据点,为了收买他,特意备下好酒好饭,孟宪铭一口不吃,强撑病体在墙上用木炭写下了“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10个大字。敌人见软的不行又来硬的,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孟宪铭掷地有声,“我是中国人,不但有血有肉,而且是有骨气的,宁死不投降。”敌人招数用尽,一无所获,只得将孟宪铭押往赤城。在赤城监狱中,敌人继续对孟宪铭使用各种引诱和酷刑,孟宪铭同志始终坚贞不屈。1944年8月,与杨克南等36名革命志士一起,被敌人杀害于县城西龙门道的乱杂坟,时年35岁。临刑前,孟宪铭视死如归,昂首阔步走出牢门,用京剧大唱:“骂一声汉奸卖国贼,我为国家一死万古美名扬……”。为了继承先烈遗志,1945年,赤城县人民政府决定将烈士牺牲的地方原龙门道改名为宪铭村(即现在的宪民村)。 其它的事情,老人都说不清楚了,但是提供了一个消息,君子堡也有个老人叫董全明,也参加过革命,这个人还在。老人们虽然对当年的情形记忆无几,但是很愿意诉说,也许平时他们口中的这些事情没人愿意倾听。临了告别,大家合了一个影。我和庞占玉老人握了握手,说了些祝福的话,便告辞了,在上车的时候转身回望,王登云老人的手正伸向我。原来他也准备和我握手,但是我没看见便起身了,老人的手一直伸着,我赶紧过去和老人握住。这时我忽然有一种悲悯的感觉,这些老人都是当年参加过战斗的英雄,而今耄耋之年有谁还惦记他们,他们想说当年的革命情形,但是记不得很多,那种欲说又止,盼人倾听的感觉在老人们的表情中显露无遗。离开的时候老人一直向我们的车挥手,反光镜中老人们的身影越来越远。 我在车上不停的想我们做这些文化工程的意义,教育后人当然重要,其实更重要的是把这些临近离世的曾经参加过革命的老人们整理出来,即使我们没有办法把他们的事迹逐一记录,起码听听他们的诉说,这种诉说仿佛让他们回到那个战火烽烟的时代。听他们诉说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更是对他们的一种敬仰。 从马营出来,我们回往君子堡,找寻老人们所说的董全明老人。君子堡,始建于明代后期,南距马营二十里,北距马莲口边墙六里。君子堡是马营的前卫城,一旦敌人突破头道边,君子堡拒敌,马营可以有充足的时间调兵,东有独石口,西有松树堡,南有云州堡。相比马营,君子堡是个小堡。堡城城垣不大,虽遭破坏,但轮廓依旧。此地也曾经是龙(关)崇(礼)赤(城)第十区公所驻地。到了君子堡打听董全明,正好老人在小买铺,便和老人攀谈。可惜的是老人一九四六年才入伍,对抗战时期的事情并不知道多少。好在他的妹妹叶有莲(同胞兄妹,后妹妹送给叶家,故姓叶)倒是知道一些事情,随行的郝姐对她的讲述做了详细的记录。叶有莲老人的丈夫参加过游击队,袭扰过谷嘴窑子日伪据点。 告别了董全明老人,便从了君子堡出来。本想奔谷嘴窑子探访当年的日伪据点,但是由于不认路,误入了马莲口村。既来之则安之,问询村里有岁数大的人?还真有一位。老人名叫杨玉明,一见面先问我们是哪里的,我说是莲花滩的,老人两眼圆睁,仿佛有些生气,问我:你莲花滩姓什么?我一时语顿,于是详细说明来意,我们是为了丁庄湾文化工程的事来的,老人才有所缓和。老人说莲花滩的人他都认识,包括小梁底的人,从没见过我们,觉得我们是假冒的,所以才生气。老人是党员,党性很强,对党和政府,尤其是毛主席一代的领导人非常信仰。老人当年参加过游击队,袭扰谷嘴窑子就是他们干的。谷嘴窑子日伪据点设置谷嘴窑子的小山上,上边还修建了墙体,由于日伪武器先进,而我游击队武器落后,每到据点时,都不敢靠近,因为谷嘴窑子据点在山包上,地势很好,临近了就成活靶子了。他们每次靠近都在步枪的射程之外,没有重武器,也端不掉据点。而守卫的日伪也不敢下来,这样双方就僵持着。但是山坡上的日伪据点没有水井,他们吃水得到山下挑,于是晚上游击队就去填井。等到了白天,日伪军下了发现井被填了,就去村里抓劳工再去掏井,其实他们抓的这些人有很多就是游击队的,也就是他们把井给填的。他们晚上袭扰日伪,白天就装成农民。这样一来一往,经常把井晚上给填了,白天再给掏。时而在晚上偷偷的贴些标语,时而在安全距离骂阵,但是都没造成多大的损失。后来日本战败,这个据点的日伪就撤走了。 老人有声有色的讲述这些往事,同时又讲述了莲花滩的庙会、马莲口的庙会等内容。临告别前忽然问我,你们既然是搞纪念馆的,给我弄四卷画。大家一时不知所然,老人又解释道:就是毛主席、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那四卷画。哦!我明白了,他所谓的“四卷画”就是文革时候常见的四伟人像。提出这个要求后,老人的眼睛泛着光芒,仿佛这四卷画他期待了已久。我答应了他,说等下次来给他带来,老人高兴的笑了。并一再向我们“告诫”,现在是好时代,要珍惜生活,要爱党爱国。他们这一代老党员对党的忠诚度让我非常感动,共产党依旧是他们心中永恒不变的信仰。我心想一定要给老人实现这个愿望,老人八十多了,朝不保夕。为了他这份信仰,也为他这份忠诚,我决不能食言。后来回县后,第一时间从网上购买了这四幅伟人像,在后来去丁庄湾的时候,专程给老人送去。老人收到画后,似乎有些哽咽,连说:真可以,真可以。也许这“真可以”是对我们文化工程的认可,也许是对我诚实守信的认可。送画的时候,他儿子着急忙慌的跑回来,厉声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也许他以后我们是骗子呢,在老人和我的一齐解释下,才解除误会。送完画,挥别杨玉明老人,老人久久不愿离去,直到目送我们离开,这也是后话了。 从马莲口村出来,我们拐进谷嘴窑子,探访当年的日伪据点。果见一小山岗,上边似乎还有建筑的痕迹,山下有一口水井,不过现在是村里的吃水井。由于夏天,村里人大多下地劳动,没见着人,时间也快到中午了,我们便起身前往丁庄湾。 丁庄湾陈列馆的主题建设基本完成,浮雕墙已经安装完毕,正在调色喷漆。我们到的时候,正好莲花滩的领导也带朋友来玩。大家看了个大概,便要离开。临行前,领导问我们去乡里吃饭吗?原来行程是打算去的,因为筹备丁庄湾陈列馆曾经和乡政府打过招呼,走访路过莲花滩,中午可到乡里吃饭。我看也别给政府添麻烦了,便拒绝了,于是我带着她几个组员便前往西辛营吃饭。 西辛营曾是赤(城)源(沽)联合县第十区公所驻地,当时的赤(城)源(沽)联合县只包括莲花滩和西辛营的部分区域,而我县其他区域则属于伪宝(昌)源(沽)联合县。当年西辛营也设过日伪据点,好像是伪警察署,后被八路军攻克。听老人说,当时西辛营的日伪据点,日本人只有一个,此人叫海老元(音),此人并不坏,没干过多少缺德事,他还挺喜欢小孩子,经常给孩子们糖吃。日伪撤后,原来的据点改成了学校。如今的西辛营趁着农村面貌改造提升的东风,整体面貌和基层设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西辛营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区域面积不是全县最大,经济基础也不是全县最高,地理位置在沽源所有乡镇也不是异常突出,但此地的餐饮业非常发达,大小饭馆小二十个。而莲花滩、小河子乡根本就没有饭馆,也许是西辛人豪爽好吃罢了。 吃过午饭,我们回了趟柳石窑沟,这里是我的老家。村里参加过革命的人不是很多,我知道的有两位,一个叫宋金宝,在解放战争中当过连长,负过伤,立过功。另一位叫李树山,参加过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解放后渡江参加过抗美援朝。可惜的是两位老人都在前几年去世了,唯一能看到的是李树山老人留下的一些勋章和“献给最可爱的人”水杯。从民政局查询,柳石窑沟还有两位解放前的烈士,叫张文成和张孝贵,他们都是骑兵三师的,在高山堡战斗中牺牲,但是问询了许多老人,对二人的情况并不知情。还有一位是我的堂兄,名叫黄福,在我出生的时候去怀来当兵,后来牺牲,也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从柳石窑出来又驱车返回莲花滩,最后一站是榛子沟村。榛子沟村是莲花滩乡一个示范村,出了一个很有能力的女支书王文花。我们前往榛子沟村的泉子沟自然村。泉子沟风光秀丽,有很多山货,夏天人们多去采摘黄花、蕨菜等。此去泉子沟除了走访革命年代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的老家也是泉子沟的,我们一支黄姓在民国初期从泉子沟迁出,泉子沟还有当家子的黄姓。组员几位姐姐在和王文花大姐闲聊的时候,我去我们的一个堂叔伯哥哥家坐坐,这也是我第一次来此地探亲。刚往下走,老远迎出一个人来,我们没见过,但肯定是亲戚。不知怎么称呼,相互说明,按辈分来他管我叫叔叔。他父亲正是我的堂叔伯哥,老哥今年七十六岁了。一家人很是热情,问了些老堂哥关于家族的事情,便告辞了。本后回头想后头再去看看老堂哥,可是在我们这次见面后没过多长时间,他便去世了,这也是很大的遗憾,俗话说:七十不保月、八十不保天。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对于文化工程的走访事宜总有一种紧迫感,生怕打听到消息,等准确前往的时候老人没了。这种事情时有发生,我们组的沫末姐有一个姑父在赤城,他当年也参加过革命,本打算抽调时间去趟赤城,可是没过多久,老人便去世了,只都是遗憾。 此次走访虽然没得到多少一手资料信息,但给我最大的感触是我们做的这个文化工程的意义。抗战胜利七十周年,而参加过抗战的老人们现在都以耄耋之年了,健在的没有几个了,也许等抗战胜利八十周年的时候,我县范围内的抗战参与者或亲历者几乎就不存在了。即使现在健在的能清楚说明当时情况的老人已经非常少了,而他们也渴望留下些什么,那怕是一个故事、一个名字。而我们做的文化工程是一个亟待做的工程,这个工程不仅仅是一个陈列馆、一本书,更大的意义是挖掘整理这些资料,就算仅仅知道这些老人的名字,就算是在我们的作品中提到他们,这也许是对这些老人最大的慰藉吧。 夕阳西下,光影从坝头的山坡上斜射下了映在我的眼前。而我的心潮久久不能平静,和王登云老人的握手,答应杨玉明老人的伟人画像,那些老人充满沧桑的脸颊、那经过岁月洗礼的眼神,那一份份的希冀时刻在我脑海中回荡。记住这些老人,用文字记住这些老人,传承下去,这也许是一个沽源文化爱好者的责任吧。 |
|
(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扫码关注沽源网

精彩内容看个够
张家口今日热点

各区县的新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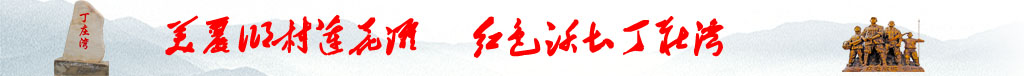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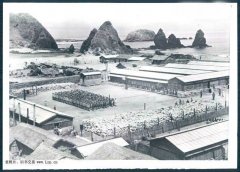
 冀公网安备 13072402000037号
冀公网安备 130724020000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