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幻想着我所落户的村庄是山青水秀,炊烟袅袅,小河潺潺,鹅鸭满塘,牛羊肥壮,我盼望着在“麦浪滚滚闪金光,棉田一片白茫茫”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幸福的生活;小资情调洋溢于胸。 可是当到了所在的村庄后,眼前的景象顿时使我感到困惑,几乎百分之百的土坯苇草顶的房屋,没有瓦屋,全村只有一家的房屋的基础是砖的,而且砖墙也仅有40公分高。我们的到来,吸引了一大堆看热闹的群众。因为是冬天,小孩子穿得是破旧的空心棉袄,光脚套着裂口的棉鞋,爱淌鼻涕的小孩因为擦鼻涕,所以胸膛面前亮光光的似上了一层蜡。上了年纪的人穿得是那种不用皮带、口袋似的蓝布大腰的裤子,上身穿得是老式棉袄,腰间不是扎了条布条就是扎了根草绳,脚上套着“毛窝子”(用草和鹅鸭毛混合编织的鞋);极个别家庭条件稍微好些的,头上戴着栽绒的三块瓦棉帽,身上穿着蓝大氅(棉大衣)。初到的两天,队里也没安排事情,我就在村庄前后乱转,眼前没有山,也没有小河潺潺;湖倒是有,但离村庄有三、四里路,村里有个不大的塘,很脏,没有满塘的鹅鸭,也没见肥壮的牛养,生产队养的牛倒是有几头,但并不肥壮,牛屋里整天是烟雾缭绕,熟悉了以后就会发现,只要是天阴雨雪或无事的时候,总会有不少人挤在牛屋里闲聊取暖。偶尔有说书的人来,牛屋又变成了剧场。 卫生条件和城市相比自是没法说,当地人几乎不刷牙,顶多用水漱漱口,只有几个上过学的青年人和退伍兵有这个习惯,穷,买不起牙膏就用盐替代;吃得又都是杂粮,所以,大部分人的牙齿与牙花交界处象有一层糨糊似的;有一次村里的一个涂姓大爷请我写一封信给他当兵的儿子,在糊信封口的时候,他居然把大拇指甲横着往嘴里一刮,用臭哄哄的牙垢作糨糊,把信给糊了!我看的是目瞪口呆,他还说,和糨糊一样的,也很粘的。 记得当天到的时候,生产队安排我们在一户社员家吃的中饭,当他们端上有小脸盆大小、薄薄的、黄灿灿的玉米面饼时(当地人叫秃头饼),我还认为是鸡蛋摊得呢,心里想,他们穿得不怎么样,吃得不错嘛;待一口咬下,粗糙的饼被咀嚼开后,满嘴都是,捣鼓半天才咽了下去。此外,由于盐碱地多,喝的水也有点咸。 理想被现实打破,困惑也很快被现实解开。年少的我之前并没有接触过多少社会生活,虽然也在农村学过农,可那是在江南,是城市的郊区,那的农民生活比起苏北要强很多啊!毛主席的号召,青年人的激情,使我很快就基本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二、三个月之后,我就和当地的农民“同流合污”了。 寒冬蜡月,村庄里的青壮劳力都去上河工了,大领导队看我长得矮小,照顾我没让我去。让我和4队的知青小聂、3队的老韩、5队的知青小孙、8队的老李组成了看青队,平时就在麦田里巡视,防止社员家的猪跑到田里啃食麦苗。 那时,每个生产队的牛屋和仓库都在村庄的外口,与自己队的田地很靠近,我们巡视后往往会在就近的牛屋休息。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灿烂,你会发现在牛屋南边的墙根下坐着一排老年人,嘴里叼着个旱烟袋一边吹牛,一边解开裤腰,眯缝着眼睛聚精会神的在捉虱子,刚开始的时候,我很好奇,不知道他们在那干什么,近前一瞧,妈呀,他们的裤腰内布满了一粒粒长椭圆形、鱼子般大小、略带琥珀色的东西,一问才知道那是虱子籽!只见他们从容不迫的用手拈起虱子籽,用两个大拇指的指甲对挤,“啪”的一声,虱子籽就挤破了,有时候,他们还会把虱子籽放进嘴里用牙齿咬,嘴里还自言自语的说“干了一个,又干了一个。”十多个人整齐地坐在墙根下,捉虱子的动作虽不整齐划一,但注意力非常集中,旁若无人,倒也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没多久,我也过上了虱子,也学会了他们的动作。 来年小麦扬花的时候,又一种小东西在侵扰着我,那就是跳蚤,这东西也只有鱼籽大小,酱褐色,形状似折拢起翅膀的蝴蝶,行进起来一跳一跳的,蹦起来有三、四十公分高,专门在你的床上伺机吃你的血,捉也不好捉,身上常常被咬的斑斑点点,盖的被子上也是血迹斑斑,洗也洗不掉;而且这东西咬人是奇痒无比,晚上经常被小东西骚扰的睡不着。当时,在我们当地有这么一种口头禅“手挤虱子如开枪,小麦扬花,蛤蚤成把抓。” 待我1979年回城的时候,虱子和跳蚤已不很多了,可能是农村的卫生条件已有改善和农药使用普遍的缘故吧。 |
|
(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扫码关注沽源网

精彩内容看个够
张家口今日热点

各区县的新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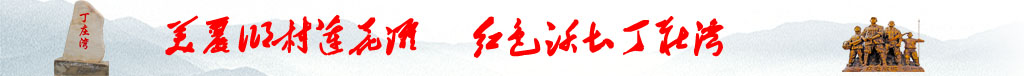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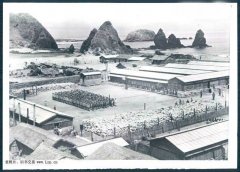
 冀公网安备 13072402000037号
冀公网安备 1307240200003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