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北又是个靠天吃饭的地方,老乡的日子不好过。知青去的第一年,吃国家统一供应的配给粮,主要是玉米面,很粗很陈的玉米面,和现在超市卖的玉米面根本是两回事儿。加上我们刚走出家门,都不会饭。要在农村生存,必须学会蒸玉米窝窝。我们遇到了两大难题,一个是烧火问题,不会烧土灶,经常是烟大火小,不给力,蒸出的窝窝半生不熟,又急着上工,只好稀里糊涂地塞到嘴里走人。另一个是用碱的计量问题,知青轮流做饭,谁也没经验,有的人把碱面放多了,黄馍变成棕色,苦涩的难以下咽;有的人把碱放少了,酸的直倒牙,特别难吃。没有蔬菜,顿顿盐水熬萝卜汤。没多少日子,肚子里的油水刮得精光,经常饥肠辘辘,大家发现,嘴越来越馋了,劳动休息时,开始围在一起精神会餐,回味起在北京吃的美味佳肴:红烧狮子头、红闷肘子、红烧排骨、红烧鸡块儿——俗话说,馋咬舌头,瘦咬腮。有人吃饭时直咬舌头,实实在在想吃肉了。 饿得撑不住了,开始各打各的主意。有的男生找茬进城,走几十里山路,到饭馆暴撮一顿,虽然,延安城里的饭也不怎么样,但总有点油水,哈好解解馋;有的和老乡套近乎,蹭上一顿半顿的;有的让家里寄点好吃的东西,改善改善。我从小爱吃甜食点心,有一次到河对面的供销社买东西,发现有散装饼干不算太贵,所谓饼干,也不是城里卖的那种,非常粗糙,样子很难看,味道更别提。我试着买了半斤,一尝,怎么一股煤油味,我问售货员怎么回事?她还挺不耐烦地说:“农村点煤油灯,还能没有煤油味儿!”理直气壮的,反问起我。我不是馋吗?又没别的东西可吃,就它吧。拿回队,悄悄放在箱子里,实在又饿又馋的时候,就掏出几片来打牙祭。对我,还是有点作用,吃完了再去卖半斤。管他有没有煤油味儿,饿了,馋了,吃什么都是香的。 记得有一次,知青集中到公社开会,中午管一顿饭,熬了几大铁锅玉米饭(去了皮的玉米豆),就的是老乡腌的碎菜(各种菜切成丝放一点盐腌的,有点酸味,有点咸味),大伙可吃到一顿正经饭了,盛了一碗又一碗,狼吞虎咽,三下两下就吃完了。周围老乡看得都傻眼了,有人说:“这是咋得咧?看把娃娃们饿成啥样了?真是,慢着抢,慢着抢,还有呢。”不一会功夫,几锅玉米饭,“洗劫一空”。这顿饭,至今回想起来,都余味无穷。 我们队有个高中女生,不知从哪儿搞了一个泡菜坛子,做了一罐泡菜,泡的是水萝卜、莲花白、芹菜。吃黄米饭时就着,那叫一个香。十几个人一天就消灭光了,吃完赶紧再泡一罐儿。不过,再饿、再馋、再苦,再累。我都会自己扛着,不给家里说,写信一概报喜不报忧,让家里放心。 第二年,我们有了劳动的收获,分了各种杂粮,学会了捞黄米饭、熬夥饭、压荞面饸饹、戳凉粉、腌碎菜、积酸菜等许多陕北饭。有个北京干部姚正秉是北京某副食公司的经理,有一手做黄酱的绝活,他给我们窝了一大盆北京风味的黄酱,在缺肉少油的岁月里,成为我们打牙祭的最好替代品,黄米饭拌黄酱,玉米窝窝抹黄酱,菜里拌黄酱,香极了。 我在村里当了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以后,和老乡的关系更贴近了,逢到农村的节日,都会被悄悄叫去打牙祭。农历二月二,是龙抬头的日子,家家户户炒豆豆,有的是炒小面疙瘩,有的是炒小麻子籽,有的是炒豆子,娃娃们这一把那一把,拿送来给我;清明节我们村兴涮荞面煎饼,是个技术活,没两下子,涮不好,一张张薄乎扇扇的半透明的煎饼,卷上绿豆芽、炝土豆丝,沾上蒜汁,绝对精品,我有时会同时被几家邀请,如果你不去会被视为瞧不起人家,所以必须应酬,我就一家尝一张,一会儿,就吃到嗓子眼了。 |
|
(责任编辑:红枫网络) |
扫码关注沽源网

精彩内容看个够
张家口今日热点

各区县的新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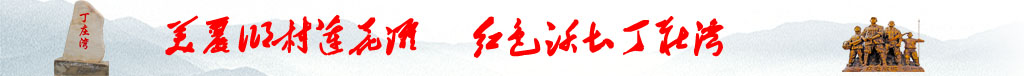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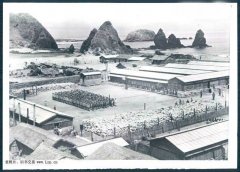
 冀公网安备 13072402000037号
冀公网安备 13072402000037号